国家公园,勿忘荒野(新论)
荒野作为一种生命之源,有野性之美,具教化之功。作为维护荒野价值的国家公园,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一种精神寄托,也显现一种思想力量
始于100多年前的国家公园体制,是目前国际公认的行之有效的荒野保护模式。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权威认定,国家公园“在储备地球自然场域、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可持续使用自然资源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家公园名录已涵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
在国家战略层面,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起步于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虽然起步较晚,但在国家顶层设计下,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势头迅猛。截至目前,已设立三江源、东北虎豹、大熊猫、祁连山、湖北神农架、福建武夷山、浙江钱江源、湖南南山、北京长城和云南普达措等10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国家公园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自然保护区,更不是一般的旅游景区,其设立的初心,是要保护荒野的原生态和完整性,并把它们完整地留给子孙后代。而以国家公园的形式对荒野进行保护,更体现了荒野独特的价值意义。
荒野被视为生命之源。荒野是所有生命孵化的基质,包括人类自身。在荒野中,旧的物种谢幕,新的物种产生,物种生命体系和自然生态系统不断更新。走向荒野的哲学家罗尔斯顿曾察觉到人的手掌与蝾螈脚掌之间具有某种亲缘关系,由此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保留和保护荒野,因为“荒野是一个活的博物馆,展示着我们的生命之根”。在荒野自然中,生命的奇迹不断上演,自然界的每一种生物与非生物都具有生命力,都是值得人类尊重和敬畏的生命力量。
荒野有野性之美。相对于钢筋水泥丛林结构的现代城市,荒野是一个呈现着野性之美的完整稳定的生命共同体,有着更加纯粹和本真的生命特质。从荒野中走来的人类,不仅应该是有着文化气质的文明人,还应该展现出自身的本真气息。作家梭罗就曾被这种本真和纯粹的野性之美深深吸引。他离开文明的城市,来到瓦尔登湖畔,住进了自己建造的小木屋,独自体味荒野的野性之美。梭罗坦承:“我之爱野性,不下于我之爱善良。”在大自然的野性之美中,梭罗感悟到了文明荒漠中的野性绿洲,并由衷发出“生于斯,死于斯,葬于斯,此生无憾”的感叹。
荒野具教化之功。日益厌倦都市文明的后期印象派大师高更,远走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并在那里创造出自己最伟大的作品《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也许只有在原始的蛮荒与宁静里,高更才能如此深刻地领悟人类的历史命运。其实,作为人类的一种情结和象征,荒野一直承载着我们的精神寄托,并参与塑造着人类历史。早在19世纪末,历史学家特纳就认为荒野具有塑造民族性格的教化功能。其“边疆学说”正是对这一判断的系统论证。
可见,作为维护荒野价值的国家公园,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一种精神寄托,也显现一种思想力量。在这里,人们可以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净化身心,思考和探究存在的终极意义与价值;在这里,勤劳、勇敢、独立、自由、创新等民族性格有可能得以重新塑造。无论是在生存意义上的自然环境基础上,还是在宏观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甚至是在地球生物圈意义上,“荒野”都是我们必须予以重视并保护的。
(叶海涛 作者为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姑父一巴掌扇倒两岁半幼童被行拘,“一家人
姑父一巴掌扇倒两岁半幼童被行拘,“一家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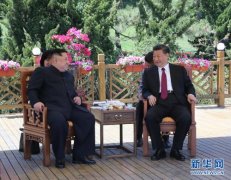 人民日报海外版:中朝加强战略沟通意义重大
人民日报海外版:中朝加强战略沟通意义重大 三亚学院校长陆丹:创办一所大学 读懂这个
三亚学院校长陆丹:创办一所大学 读懂这个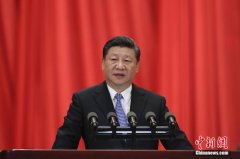 新华社评论员:感悟“千年第一思想家”的真
新华社评论员:感悟“千年第一思想家”的真 胡星斗:推行免费医疗及“三免”时机已成熟
胡星斗:推行免费医疗及“三免”时机已成熟 海南省长沈晓明:把资源留给后人也是政绩
海南省长沈晓明:把资源留给后人也是政绩 直播间不是法外之地!薇娅偷逃税款被罚再敲
直播间不是法外之地!薇娅偷逃税款被罚再敲 面对违规学生 教师缘何不敢管、不能管、不
面对违规学生 教师缘何不敢管、不能管、不 “潜龙三号”试验性应用首潜归来 带
“潜龙三号”试验性应用首潜归来 带 千年古县东阿发展“绿色经济” 激发
千年古县东阿发展“绿色经济” 激发 中国“一箭五星”成功发射“珠海一号
中国“一箭五星”成功发射“珠海一号 中国各地盆景大师携精品上海竞艺 流
中国各地盆景大师携精品上海竞艺 流 10月新规来了!事关身份证、车子、电
10月新规来了!事关身份证、车子、电 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完成首个航道主
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完成首个航道主 北京一律所发文拒聘川大毕业生,第三
北京一律所发文拒聘川大毕业生,第三 代理商揭秘张庭公司套路:把代理商称
代理商揭秘张庭公司套路:把代理商称